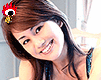| 南方周末:上海居不易 上海人被房子改变的命运 | ||||||||
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
| http://house.sina.com.cn 2005年04月21日17:30 南方周末 | ||||||||
|
大连路是虹口区和杨浦区的分界线,东侧是杨浦区,房子都是黄颜色的,要比西侧的房子每平方便宜几千块。4月10日下午,邵跃中站在这条分界线边上感慨说,说什么也不能从街对面搬到这边的黄房子里来住。他是一个上海式的“百万富翁”,靠打零工过活,月收入大概700多元,财产的“95%”都在家里那套二室一厅的房子上。 邵跃中说,他并不是抱有“地域即阶层”的传统观念,只是不想卖掉现在的房子。“
几年来,房屋买卖正在催化上海的阶层格局的变化。 炒房与否分开两个阶层 去年以来,上海房价持续走高,连使用了10年以上的二手房价格也一路飙升。去年10月中旬,38岁的杨学兵通过中介公司卖掉了一套“老掉了牙”的二手房,赚了12万,然后就把炒楼生意全部交给妻子去做,自己撤出来。“我们做得小,没必要两个人都付出精力,我想抽身出来做做自己的专业。” 杨学兵的专业也跟房子有关,装修设计。如果不是通过装修认识了一些炒房者,他也不会涉足这一行。他说话声音很轻,穿着再普通不过的蓝衬衫,除了开着一辆帕萨特外,看不出有任何“发财”的迹象。 相比之下,刘卫光就显得很气派。他面色红润,身着一身白色西服,右手中指上戴着一个很大的金戒指,手拿公文包,一坐下来就侃侃而谈。不知其背景的话,你同样很难想象他的身份。 “炒房当然很赚钱,而且越是炒得不辛苦的人越赚钱,他们不光是靠眼光和资本,还靠各种信息、交情。”杨学兵说。跟他熟悉的炒房者中最有钱的一个,是上海本地人,以往有兼做股票和公司的经历,能够拿出来炒房的资金至少有5000万元,不过有多少是银行的贷款就说不清楚了。 “有很多人就是炒对了一次房,就突然间发了财。”杨学兵说,“有喜欢专心做一个楼盘的那种,一两个月就能用50多万赚到好几倍。” 最初他“朦朦胧胧的”,被朋友带着炒房,渐渐地发展到去年同时操作四五套房子,终于升格到了上海炒房阶层里的“普通级别”。至今他还记得自己炒的第一套房子在浦东花木路,贷款四成,用了两个半月,赚了5万。 刘卫光则是一个曾拿到53万元拆迁补偿款的老上海,虽然外表气派,其实是个穷人。 刘家原本是一个中上层的上海家庭。82岁的父亲刘宗沛是某集团高级工程师,弟弟刘卫光1988年下海做生意。哥哥刘卫平一家三口。在2005年春节前,还未去世的102岁的奶奶也跟他们住在一起。 拆迁之前,刘卫光一家四代7口人,住虹口区东宝兴路一个弄堂里,紧挨着四川路。这里是虹口区的中心地带,在整个上海市也算得上是风水宝地。就在离刘家不到两站路的一块地,就是当年上海地块拍卖的“标王”,如今已经盖起了新楼。据一位业内人说,这座楼仅成本价每平米就在1.6万元左右,至于售价,“不会低于4万元。” 除刘卫光自己有一间房之外,刘家的其他人合住一座两层小楼,和许多精明的上海人一样,刘家将小楼搭成了三个独立空间,分别住祖孙三代人。这样,刘家平均每个人的住房约合七八平方米,在上海老弄堂里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居住水平。 2002年底,东宝兴路开始拆迁,经过“艰苦谈判”,刘家争取到每平方米合计7000元的拆迁补偿,共计53.2万元,在总共708家拆迁户中,这是一个居中的数目。从2003年4月22日起,刘家搬到一处过渡房住了一年。早在2002年拆迁谈判时,刘卫光就看中闸北区两套房子,房价每平方米4500元,用拆迁款再加上一点自己的积蓄,可以买到两套两室一厅。这样哥哥自己住一套,刘卫光与父亲、祖母共用一套。由于当时补偿款不知能拿到多少,也没钱付首付款,买房的事就拖了下来。 到了2003年6月,补偿款到手,此时看中的房子涨到了6000元/平米,拆迁款只能买一套半了。再到后来,该地段通了地铁,房价升到了现在的8000元/平米,这样,刘家买房的事彻底搁在一边了。刘卫光和刘卫平各租了一套房子住,每月付房租约1000元。 按照杨学兵的逻辑,刘卫光当初如果把53万元用于炒房的话,如今的境遇可能就会完全不同。 刘卫光今年49岁,对自己的婚姻已经不抱多大希望:没有钱买房,有谁会上门呢?他102岁的奶奶春节期间过世,老人临死前念念不忘的,仍然是房子。 温州炒房团形成新群体 “别人看见温州炒房团炒楼,没人看见我们自己也被炒。”张丽峰说,“我们被炒的程度,比楼被炒的程度还厉害。” 她认为,通常传言中的温州炒房团的事,其实只是一些吸引眼球的特别事例,不能代表全貌。在报纸电视上,温州人动辄整个团队开过来,声势浩大,给外界的印象深刻,可是实际上,“不可能每次都像旅行团似的。”在她身边,几个合伙人都在上海有生意,可以长期留在这里观察楼市,炒房也就像上海人上班一样,成为日常功课。 在她的印象里,那种突然袭击的温州炒房团,往往是本地房地产商邀请过来的。“那种炒房团破坏力大,搞得想买那个楼盘的人人心惶惶,楼价马上就上去了。”她从来没参加过那种活动,原因是“我就在上海”。 一露面,张丽峰就解释说,自己这些天实在是太忙。果然,她的两部手机不停地响,有一起炒楼的朋友约见面谈事情的,也有中介公司打电话建议降低挂牌价的,对于后者,她的态度很蔑视。 “有的中介公司请不到好人手,做生意没眼光,提的意见全是错的。” 2002年10月,她进入上海楼市,从100万多一点儿资金开始做,做到现在翻了将近两倍,自己认为做得还算不错。她强调说,自己属于平民阶层,而且是业余炒房者,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静安区经营商铺。相比之下,职业炒房者的资金要比她多得多,“多上几十倍的也有,如果经验多的话,那就相当于庄家了。” 在她看来,房子是特别重要的东西,谁都需要。在商铺里,她雇佣了6个来自江苏、浙江的打工妹,平时她教训她们,“你们不要认为自己一定不可能在上海买到房子,只要努力做,也许就有机会。” 既然已经留在了上海,她觉得,自己既算是温州人,又算是上海人。平时她和上海人打很多交道,不过信任的朋友都是温州人。在她看来,炒楼行为肯定是抬高了楼价,“每出手一套房子都会涨”,不过要说自己对上海人有什么愧疚的话,那还说不上。 “有人对我有敌意,这个我看得出来,但是你知道他们对我更多的是什么?是羡慕。”
|
| 新浪首页 > 房产 > 专题 > 10万炒房一年赚上亿 炒房魔术揭密 > 正文 |
|
| 新浪房产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:010-82628888-5482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| About Sina | 广告服务 | 联系我们 | 招聘信息 | 网站律师 | SINA English | 会员注册 | 产品答疑 Copyright © 1996 - 2005 SINA Inc.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四通利方 新浪网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