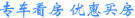在“媒介开发”竞标会截止后,伊东先生曾经很自豪地对我说:他这次的设计方案曾经决定过日法会馆的整体构造。他的那种神情和语调告诉我,他对自己的这次工作非常的满意。“日法会馆”最终被设计成一个中间悬浮着几个“凸透镜”的“玻璃箱”。而那些“凸透镜”实际上只是一些平平的石板,只因为它们像水泡一样上下膨胀,厚度薄,从远处看过来,就像悬浮在空中一样。这种透明的玻璃墙,变幻的悬浮体,在伊东先生以后的作品中也经常出现。但是,在当时的我看来,悬浮的凸透镜与建筑的整体构造毫无关系,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件华丽的装饰品。但是当时伊东先生曾对我说过一句话:这一提案如果不被采纳,对他将是最大的打击。那种语气让我也情不自禁地感染了他的那份自信,确信他的作品一定会得到承认。
在看过“媒介开发”的平面设计图及模型之后,我更加由衷地承认了伊东先生的说法。这种悬浮建筑与以前的框架建筑不同,与墙壁建筑也不同。在我印象中,欧洲某处有一高压铁塔采用的就是这种构造。而这次的设计中,石板的重量将完全由铁塔承受,更是一种崭新的建筑方式。伊东先生的设计图,让人联想到海洋中的海草,还有那极具透明感的模型,与这种建筑方式不谋而合。新型的建筑方式,配以独特的表现手法,使这个设计方案更具魅力。而各层的设计也别出心裁,每层的地板上穿有许多圆形的小洞,被用来做电梯、各种设备或吊灯的中心轴孔。但由于在地板上穿孔时毫无规律可言,所以与以往的建筑不同,用户在进行室内装修时,完全没有任何规律可寻。在以往的框架建筑或墙壁建筑中,内部构造本身就是该建筑所给出的一种“暗示”,用户也就自然而然地可以、而且必须依据该暗示进行室内布局。而这栋建筑不同,虽然这些杂乱无章的中心轴孔也具有一定的特殊的约束力,但用户基本上可以自由地发挥,所以建筑的最终布局是完全无法预测的。
这一建筑可说是伊东先生的独创,是伊东先生在“日法会馆”后更进一步的创作。这栋完美的建筑,不愧为伊东先生引以为豪的一幅作品。 但是,这一建筑真正的意义不仅仅如此。伊东先生自身的这种独创性、一贯性被周围的人所认同、所共享的这一过程其实更为重要。本属于伊东先生一人的思想、理论,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社会共有的思想、理论,换言之,伊东先生的外部世界与之内部世界产生了共鸣。而正是这种共鸣,使得这一建筑成为了一栋非常自由的建筑,这一点相信是伊东先生也没有预想到的。所以,也可以说,在伊东先生的想法逐渐被接受、被共享的过程中,伊东先生自身也在发生着变化。因为当一个人的想法超越了个人的局限,升华为大众理论后,所有承认这一理论的人就都成为这一理论的主体。所以这一建筑也不再是伊东先生一人所有,而成为众人共同为之努力的对象。在这一变化过程中,伊东先生必然要受到相应的刺激,必然要发生一定的变化。现在看来,伊东先生是积极地利用了这一变化,使其以后的设计更上了一层楼。 虽然保持伊东先生最初想法的完整性,不能说是毫无意义,但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必要去拘泥。在伊东先生的内心应该也有这种超越自我的渴望。也正因为如此,最初的造型虽然也很美,但只有超越了个人的局限,最终的建筑才能更丰满、更完美。只有当一个建筑师的想法、设计被社会所接受,外界与之发生共鸣时,他所建的房屋才可被称为“建筑”。一栋建筑无论如何的独特,如果设计者只想坚持并推行自己的初衷,而不追求与外界的共鸣,那这栋建筑最终也只能成为一间毫无生机的“房屋”。伊东先生的这栋建筑,再次让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一道理。
吴建斌辞职,3000亿碧桂园发生了什么?
挖个坑,埋点土,数个12345……自己的土,自己的地,种啥都长人民币![查看详情]